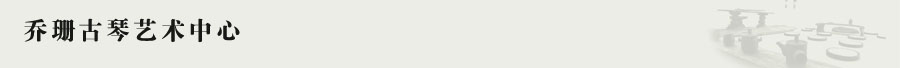- 人类思想、文化、艺术中的有些成就,其实是很难去进行分析、解说的。比如书法中的王羲之、绘画中的梵高、文学中的苏东坡、音乐中的莫扎特,比如《圣经》。他们的不可解说,是因为他们的境界太高,常人要真切地看清他们的面貌、理解他们的精神,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说我尚有胆气对琴文化的诸多方面说三道四的话,说管平湖先生的艺术,就十分地没有底气了。但因为热爱,因为迷恋其仰之弥高、俯之弥深的境界,不说,不能表白一种情感。而且,我个人认为,管先生的琴,代表着古琴艺术的最高境界,谈古琴不谈管平湖,是极大的缺憾。所以,勉力说一说。先来看一看管先生身边的人都是怎么说管先生的。当代著名学者、收藏大家王世襄是我非常钦仰的先生,他的学问,做得不同凡响,做得美。王先生与管先生少年时便相识,且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是管先生的琴弟子,王先生便与管先生相熟相知。在王先生的《俪松居长物志·家具类》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九四五年自渝返京,此为最早购得之黄花梨家具。入藏目的,并非作为明式平头案实例,而仅供弹琴之用。时荃猷从管平湖先生学琴,先生曾言,琴几之制,当以可供两人对弹之桌案为佳。两端大边内面板各开长方孔,藉容琴首及下垂之轸穗。其优点在琴首不在琴几之外,可防止触琴落地。更大之优点在学琴。师生对坐,两琴并置,传授者左右手指法,弟子历历在目,边学边弹,易见成效,一曲脱谱,即可合弹。惟琴几必须低于一般桌案,长宽尺寸以160*60厘米为宜。开孔内须用窄木条镶框,光润不伤琴首。予正拟延匠制造一具,适杨啸谷先生移家返蜀,运输不便,家具就地处理。予见其桌案适宜改作琴几,遂请见让,在管先生指导下,如法改制。平头案从此与古琴结不解之缘。平湖先生在受聘音乐研究所之前,常惠临舍间,与荃猷同时学琴者有郑珉中先生。师生弹琴,均用此案。一九四七年十月,在京琴人来芳嘉园,不曰琴会,而曰小集。据签名簿有管平湖、杨葆元、汪孟舒、溥雪斋、关仲航、张伯驹、潘素、张厚璜、沈幼、郑珉中、王迪、白祥华等二十余人,可谓长幼咸集。或就案操缦,或傍案倾听,不觉移晷嗣后南北琴家吴景略、查阜西、詹澄秋、凌其阵、杨新伦、吴文光诸先生,均曾来访,并用此案弹奏。传世名琴曾陈案上者,仅仅唐斫即有汪孟舒先生之“春雷”、“枯木龙吟”,程子荣先生之“飞泉”、拙藏“大圣遗音”及历下詹氏所藏等不下五六床,宋元名琴更多不胜数。案若有知,亦当有奇遇之感。多年来,予每以改制明代家具难辞毁坏文物之咎。而荃猷则以为此案至今仍是俪松居长物,端赖改制。否则定已编入《明式家具珍赏》而随所藏之七十九件入陈上海博物馆矣。
 王世襄所藏黄花梨琴桌且睹物思人,每见此案而缅怀琴学大师管平湖先生。一自改制,不啻为经先生倡议、有益护琴教学之专用琴几保存一标准器,可供来者仿制。是实已赋予此案特殊之意义及价值,其重要性又岂是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吾韪其言,故今置此案于家具类之首。字里行间,对管平湖这位朋友充满了敬重、怀念之情。管先生的得意弟子王迪先生在《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见香港龙音公司出版的《管平湖古琴曲集》介绍书)一文中写道:管先生在艺术上是多才多艺,但在生活上却是多灾多难。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在苦难的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战期间,黎民百姓,饥寒交迫,作为艺术家,也难以幸免。管先生一方面对艺术进行执着的追求,而另一方面还要为生活进行痛苦的挣扎。那时,他家徒四壁,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学,深夜作画。有时,为了卖一把扇面,从北城步行到南城荣宝斋。他也曾做过故宫博物院的油漆工。管先生不仅善于弹琴,而且精于制琴和修琴,现在故宫珍藏的唐琴“大圣遗音”、明琴“龙门风雨”和两个明代大柜子,都是他修整好的。
王世襄所藏黄花梨琴桌且睹物思人,每见此案而缅怀琴学大师管平湖先生。一自改制,不啻为经先生倡议、有益护琴教学之专用琴几保存一标准器,可供来者仿制。是实已赋予此案特殊之意义及价值,其重要性又岂是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吾韪其言,故今置此案于家具类之首。字里行间,对管平湖这位朋友充满了敬重、怀念之情。管先生的得意弟子王迪先生在《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见香港龙音公司出版的《管平湖古琴曲集》介绍书)一文中写道:管先生在艺术上是多才多艺,但在生活上却是多灾多难。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在苦难的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战期间,黎民百姓,饥寒交迫,作为艺术家,也难以幸免。管先生一方面对艺术进行执着的追求,而另一方面还要为生活进行痛苦的挣扎。那时,他家徒四壁,囊空如洗,不得不白日教学,深夜作画。有时,为了卖一把扇面,从北城步行到南城荣宝斋。他也曾做过故宫博物院的油漆工。管先生不仅善于弹琴,而且精于制琴和修琴,现在故宫珍藏的唐琴“大圣遗音”、明琴“龙门风雨”和两个明代大柜子,都是他修整好的。 管平湖和他的弟子们前排左起:许健、管平湖、郑珉中中后排左起:王迪、沈幼、袁荃猷一九四九年前夕,他的生活越发窘困,只好靠画幻灯片来糊口。虽然他过着“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的清苦生活,但他依然不放弃对古琴音乐艺术的探索,他每天坚持弹琴打谱和教学,数十年如一日,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关管先生的生平,资料相当少,我有幸接触过管先生的弟子,他们说得最多的,是管先生高尚的人品和出类拔萃的琴艺,其余,则是叹息管先生的清贫。可是,每一个热爱管先生艺术的人,都不免会对管先生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着迷。因为资料稀有,没有管先生的年谱,管先生写自己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因此,要描述管先生的习琴经历,理解他琴艺的构成,就显得相当困难。与管先生同时代的琴家查阜西先生在《琴坛漫记》一文中提及管先生,文字是这样的:管平湖年五十四,苏州齐门人,西太后如意馆供奏(注:似为“奉”之误)管劬安之子,父死时年稚,及长,从其父之徒叶诗梦受琴。据云其父与叶诗梦均俞香甫之弟子。嗣于徐世昌作总统时从北京人张相韬受《渔歌》及有词之曲三五,为时仅半年云。嗣又参师时百(注:杨时百,即杨宗稷)约二年,受《渔歌》、《潇湘》、《水仙》等操。民十四年游于平山(注:疑为“天平山”之误)遇悟澄和尚,从其习“武彝山人”之指法及用谱规则,历时四五月整理指法,作风遂大变云。又云悟澄和尚自称只在武彝山自修,并无师承,云游至北通州时曾识黄勉之,后遇杨时百听其弹《渔歌》,则已非黄勉之原法矣。管平湖一生贫困,与妻几度仳离,近蹴居东直门南小街慧昭寺六号,一身以外无长物矣。十三龄即遭父丧,但十二岁时父曾以小琴授其短笛(注:疑为“曲”之误),故仍认父为蒙师。管亦能作画,善用青绿,惜未成名,则失学故也。五六年来,有私徒十余人,郑珉中、溥雪斋、王世襄夫人、沈幼皆是。又曾在燕京艺校等处授琴,此其惟一职业。溥雪斋称其修琴为北京今时第一,今仍以此技为故宫博物院修古漆器,惟仅在试验中耳。问其曾习何书,则云只《徽言秘旨》、《松弦馆》、《大还阁》、《诚一堂》诸种耳。(见《查阜西琴学文萃》)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五一年,其时管先生的年龄为五十四岁,正是中年。这篇文章对管先生的介绍尽管简短、粗略,却有许多值得分析之处。管先生名平,字吉庵、仲康,号平湖,自称“门外汉”,江苏苏州人。清代名画家管念慈之子。生于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卒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管先生十三岁时遭父丧。十二岁时,管先生的父亲曾教他学过琴,是他学琴的启蒙老师。王迪先生的文章中说管先生“自幼酷爱艺术,弹琴学画皆得家传。”可见管先生的琴和画的启蒙老师都是他父亲。因为管先生的父亲在管先生弱龄之时便去世,管先生从父学得的技艺应该不多,但家学之于一个人艺术历程的影响力却不可忽视。管先生正式习琴的年代不详,按查阜西先生的文章介绍,“及长,从其父之徒叶诗梦受琴。”学了哪些曲子,也不详。而后, “从北京人张相韬受《渔歌》及有词之曲三五”,“为时仅半年”。这说明管先生在向张相韬学琴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否则,要学《渔歌》这样的曲子是困难的。而从张相韬学琴,还学了“有词之曲三五”,说明管先生曾经接触过琴歌。管先生比较重要的老师是近代名琴家杨宗稷,这一段学习的时间较长,“约二年”,学的曲子也多是《渔歌》、《潇湘水云》、《水仙操》等名曲。杨宗稷的老师是近代大琴家黄勉之,管先生向杨宗稷学琴二年,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受杨宗稷的影响。杨宗稷没有录音,但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杨宗稷的儿子杨葆元的琴音中听出管先生与杨宗稷的渊源。对管先生影响更大的应该是天平山的悟澄和尚。管先生遇到悟澄和尚以后,“从其习‘武彝山人’之指法及用谱规则,历时四五月整理指法,作风遂大变。”杨宗稷是成名琴家,又是以教学严格著称的黄勉之的弟子,管先生随杨宗稷习琴,自然接受严格的指法训练和用谱规则。那么,以如此严格的训练基础,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不同的指法和用谱规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悟澄和尚的指法和用谱规则一定有不同一般的妙处。而“作风遂大变”,更明白地说明了这种影响之大。王迪先生这样概括管先生的琴艺渊源:“管先生对古琴艺术研究极深,得九嶷派杨宗稷、武夷派悟澄老人及川派秦鹤鸣等名琴家之真传,他能博取三家水仙操等名曲之长,并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融会贯通,不断创新,自成一家,形成近代中国琴坛上有重要地位的‘管派’。”可见,管先生的琴风由三个重要方面构一是博取各家之长;二是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三是创新。这种概括与查阜西先生文中的内容略有差异,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因为管先生没有留下教琴的教材或操缦的笔记,致使我们今天非常遗憾地不能具体分析他的心得,好在他留下了大量的录音,使得我们可以直接聆听他的琴音,使我们须臾不离他的艺术,这其实是最要紧的。管先生的琴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里,我不可能、也没条件详说,只能谈谈自己听管先生琴曲的大概感受,说说我对管先生总体琴风的理解。我说过,古琴的最高境界是“清”,而管先生的琴风,正可以一个“清”字概括。声音是无处逃心的,是一个琴人内心情况的反映,是人格精神的写照。管先生的“清”,首先是人格的清洁。但凡介绍管先生的文章,都不免说到管先生的清寒,但正如桓谭《新论琴道篇》中所说: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昔富而今贫。摈压穷巷,不交四邻,不若身材高妙,怀质抱真,逢谗罹谮,怨结而不得言;不若交欢而结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相见期;不若幼无父母,壮无妻儿,出以野泽为邻,入用掘穴为家,困于朝夕,无所假贷。若此人者,但闻飞鸟之号,秋风鸣条,则伤心矣,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涕泣者也。”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也再深刻不过。正如“诗穷而后工”一样简单和深刻。管先生的生活遭遇,与雍门周描述的那些不幸之状是一样的,但管先生之高,在于他的音乐有超越悲恻的美,他的音乐有深在的悲苦,但并非形容枯悴之态。清新质朴,是天行健、君子自强的品格。老子说,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延用此说,我以为,管先生的琴乐是大悲若喜。这样的超越,似乎都没有经过任何的纠缠,没有丝毫的自怜自艾,便转化成一种与天地、山水、人格中最美好的品质浑然一体的美,不可名状。恰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他说的是诗人,用以说管先生,也是非常合适的。性情之正、人格之高,是管先生琴艺的根本,有了这样的根本,管先生是自信的,他的琴因而有了清刚之气,乐而不荒,忧而不困。管先生所弹的琴曲中,以“悲曲”居多,《幽兰》、《胡笳十八拍》、《大胡笳》、《离骚》、《乌夜啼》、《广陵散》、《潇湘水云》等,都是失意、愤懑的内涵。但他的演绎却将这种内涵引向于“清壮”,哀痛总是被转化为深沉内敛,缠绵情绪被转化为大的悲悯,成为哀而不伤的境界。“清”,在明清文化,常常只是一种平和雅致的趣味,这种雅趣当然也能远离悲苦,但不免让人触摸不到内在的悲怆,而管先生之清,是沉潜于人格精神之中的清,是比雅趣更高的一种人格境界。管先生有盎然的生活趣味,擅种花草,擅作书画,喜爱民间音乐,甚至玩鸣虫也是一流高手。王世襄先生在《冬虫篇》一文中(见《锦灰堆》)说起过管先生养虫的趣事:古琴国手管平湖,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艺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麻杨罐中喜出大翅油壶鲁,其翅之宽与长,数十年不一见。初售得善价,旋因翅动而不出声被退还。平湖先生闻讯至,探以兔髭,两翅颤动如拱揖状。先生曰:“得之矣!”遂市之而归。不数日,茶馆叫虫,忽有异音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先生曰:“此麻杨的倒拨子’耳,(售出之虫因不佳而退还曰“倒拨子”)众更惊异,竞求回天之术。先生出示大翅,一珠盖药竟点在近翅尖处,此养虫家以为绝对不许可者。先生进__而解答曰:“观虫两翅虽能立起,但中有空隙,各不相涉,安能出音!点药翅尖,取俗谓‘千斤不压梢’之意,压盖膀而低之,使两翅贴着摩擦,自然有声矣。”众皆叹服。先生畜虫,巧法奇招出人意想者尚多,此其一耳。心意之巧,趣味之富,可见一斑。性情如此之人,心中必对生活有喜悦,也必然形之于琴。而琴中所涉社会情感、山水自然,定然有更阔大、更深微的美丽,这些,一定更让管先生着迷,让管先生在于自己情感不离不弃的同时,把深沉的个人情感与广大世界的美融合在一起,在表达的同时实现了超越。这种对一己、对雅趣的超越,非常自然,一点姿态也不去做。能如此,恐怕只能说是天性使然。晋人说,“清正使人自远”。管先生的琴,骨子里清刚清壮,而又有清远之致。清远,是说一个人精神对世俗情感的超越。这种超越,以思辩的方式,或许会落入玄虚寂寞,而以艺术的方式,则在超越自我悲情的同时,与具体可感的美好事物发生联系,以美的形态呈现。管先生的超越,不同于一般的忘怀于山水,不同于简单的依傍。他的琴,更多地有着对历史情感的体贴。当他以琴声去体贴屈原、蔡文姬,去体贴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体贴那些美好而不幸的心灵,体贴山水自然时,他的个人遭际的不幸就与民族的苦难、与众生的盼望融为一体,与不朽的山水相应和,成为一种大的关怀。这种“远”,就不是于情感的逃离,而是美与美的交往。我们在听管先生的琴曲时,总能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清逸之气,一种清越的美。似乎管先生的琴中更多的是山水自然的清新而非人间情感的拘泥。这一方面与管先生的大悲悯、大关怀有关,也与琴曲题材、内涵多山水情抱有关,与管先生重要的打谱多早期琴曲有关,也与管先生的手法有关。管先生打谱的成就,举世公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他所打的谱子多为早期琴曲。《幽兰》取自《古逸丛书》;《长清》、《离骚》、《白雪》、《广陵散》、《获麟》、《大胡笳》据谱为《神奇秘谱》。这些早期琴曲,保留了大量古指法,风格、趣味与明以后有很大的差异。琴曲与中国诗文、绘画、书法等艺术一样,早期的作品质朴、厚重,更重人在天地间的直接感受,植根于生活,取源于心灵,而非生长于既有的艺术传统,因而具有更显著的原创性,艺术手段与表现内容的结合更紧密、更天然,相对于后来的趣味讲求,早期艺术更讲究格调和境界。从艺术历史的角度而言,早期艺术更“古”。琴曲也是如此,早期琴曲声多韵少,右手取音,变化丰富,却又不致于熟腻,左手则简洁,具有清劲、质朴的特点。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说过,打谱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它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这是琴曲文献多“同名异曲”的原因,也是历代琴曲传承、发展的主要方式。管先生的打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打的许多琴曲,有主要的据本,但将其弹奏录音和据本两相对照,却会发现音、谱字并非一一对应。这种改动,根据多种版本,参证考量而作出,其中也不乏管先生自己的增删。这正是古琴文化的特点,在最高意义上体现了打谱的价值。所以,他的打谱和弹奏,既是精湛的艺术品,也是古琴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管先生右手出音,均是近岳而弹,力度大,劲健清刚,很少出柔和温煦之音,显得非常劲拔、开阔,是往远开张而非往里收缩的。但因为管先生右手指甲不好,几乎没有没有甲音,出音便特别的沉厚,在峭拔的同时,不致于粗厉。古指法用得多,必然变化多,这难免造成细琐,而管先生右手出音既古拗,又在音量上非常统一,始终保持气格上的清正。管先生左手取音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吟猱多用方直而极少用圆柔,而且均是“有板有韵”,有十分严格的规矩。这便化繁为简,使旨在取韵的复杂的吟猱有了统一的个人语言。而且,管先生的吟猱用得并不多,当吟猱便明白清晰地吟猱,不当吟猱则绝不妄动。此外,管先生的绰、注也非常简炼,多取短而少用长。细加留心,可以发现管先生左手的许多取音是直接按本音而不用绰,这与绝大多数琴家取音多用绰有着分明的不同,因而更显得清隽、洁净。古琴取音不易一下子找准本音,所以要借助绰,渐至本音,管先生能直接按准本音,这当然与他无与伦比的功力有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我认为这更是由管先生对古指法的尊重、由他清劲简明的性格趣味决定的。《神奇秘谱》中有“绰”音,但大多数按音未标“绰”,这显然是古人的一种要求,管先生左手取音,正是按照古谱的风尚而做的。这样,本音和本音之间就少了许多冗赘,少了许多与本质关系不大的所谓“韵味”。对于古琴指法的用意,管先生有独到的见解。我听王迪弹过管先生传授的《渔歌》,其中的拍煞手法很特别,不同于我们听惯的那种爽利的拍煞。王迪先生说,管先生当时的解说是:《渔歌》是归隐之士的精神自况。醉于江湖,心中有所述说,却又觉得不说也罢,于是轻扣船舷,欲说还休。这里的拍煞,应该取此情况。这样的理解,找准了手法与琴曲内涵的内在联系,真是非常微妙得当。在节奏板眼上,管先生也非常有个人特点。他的曲子,节奏规整,韵律方正,急而不乱,缓而不散,语言十分统一。但这种规整,又明显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节奏特点,而是以平远、高远、深远的意图,将个人精神均衡地灌注于琴曲展开的每一个阶段。与此相关,管先生弹琴的音色、轻重的变化不大,对比小。听惯了西方音乐的人可能觉得这种音乐比较单调。其实,这正是中国艺术的特点,它不同于情绪化、戏剧化的音乐表达,避免了那种激动的表情,避免了表面的漂亮,使得情感深在,刚正而不粗厉,生动而不过敏,古朴而不枯槁,润泽而不甜腻。管先生的“古”,不是苍古,而是清新之古;管先生的“逸”,不是草逸,而是清逸;管先生的“ 寂”,不是荒寂,是清寂;管先生的“ 健”,不是一般的壮健,而是清健:管先生的“刚”,不是刚硬,而是清刚。管先生的艺术如宋元画,笔笔精到,又略无有句无篇之弊。这有技巧的方面,更反映出人的丝毫不苟且。每一个音、每一个吟猱都有来历有涵义,却又统一于大的境象,遗形得神。管先生对传统琴学的修养极为深厚。他的独特琴风,有着极为扎实的基础。因为对与琴有关的知识、技法掌握得扎实,管先生才有可能在进入中年以后成功地打出那么多古曲,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曲。在今天看来,不懂简谱、五线谱的管先生,在当时录音、辅助记录很差的条件下打成那么多大曲,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须知,这些琴曲,别说“从无到有”艰苦异常地打成功,即便是一个有相当水平的琴家,照着管先生的录音和整理谱把它们全都熟练地学弹成功,也是非常不易的。古人论山水画,有将画家分为逸家、作家者,所谓逸家,即王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元四家等天才纵逸的画家。作家即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马远、夏圭、戴进等长于功力者。而兼逸与作之妙者,为范宽、郭熙、李公麟等。前者大致是具有极高天分的艺术家,是开派立宗的人;后者为功力深厚扎实者。只有极少的艺术家能够综两者之长。管先生,可以说就是兼逸与作之妙者。传统“文化”在管先生身上是活的积淀、活的体现,他不是生活在优雅的诗文中,而是生活在生活中,他的琴,植根于中国活的传统中和他自己的生命、性灵中,其清新与自然,有如种子破土而出。管先生的琴,不是舞台表演化的,不是庭园式的,而是万壑松风,是大河宽流,是孤云出岫,是清朴之人立于苍茫天地间的磊落与坦荡。管先生,怎一个“清”字了得!
管平湖和他的弟子们前排左起:许健、管平湖、郑珉中中后排左起:王迪、沈幼、袁荃猷一九四九年前夕,他的生活越发窘困,只好靠画幻灯片来糊口。虽然他过着“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的清苦生活,但他依然不放弃对古琴音乐艺术的探索,他每天坚持弹琴打谱和教学,数十年如一日,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关管先生的生平,资料相当少,我有幸接触过管先生的弟子,他们说得最多的,是管先生高尚的人品和出类拔萃的琴艺,其余,则是叹息管先生的清贫。可是,每一个热爱管先生艺术的人,都不免会对管先生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着迷。因为资料稀有,没有管先生的年谱,管先生写自己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因此,要描述管先生的习琴经历,理解他琴艺的构成,就显得相当困难。与管先生同时代的琴家查阜西先生在《琴坛漫记》一文中提及管先生,文字是这样的:管平湖年五十四,苏州齐门人,西太后如意馆供奏(注:似为“奉”之误)管劬安之子,父死时年稚,及长,从其父之徒叶诗梦受琴。据云其父与叶诗梦均俞香甫之弟子。嗣于徐世昌作总统时从北京人张相韬受《渔歌》及有词之曲三五,为时仅半年云。嗣又参师时百(注:杨时百,即杨宗稷)约二年,受《渔歌》、《潇湘》、《水仙》等操。民十四年游于平山(注:疑为“天平山”之误)遇悟澄和尚,从其习“武彝山人”之指法及用谱规则,历时四五月整理指法,作风遂大变云。又云悟澄和尚自称只在武彝山自修,并无师承,云游至北通州时曾识黄勉之,后遇杨时百听其弹《渔歌》,则已非黄勉之原法矣。管平湖一生贫困,与妻几度仳离,近蹴居东直门南小街慧昭寺六号,一身以外无长物矣。十三龄即遭父丧,但十二岁时父曾以小琴授其短笛(注:疑为“曲”之误),故仍认父为蒙师。管亦能作画,善用青绿,惜未成名,则失学故也。五六年来,有私徒十余人,郑珉中、溥雪斋、王世襄夫人、沈幼皆是。又曾在燕京艺校等处授琴,此其惟一职业。溥雪斋称其修琴为北京今时第一,今仍以此技为故宫博物院修古漆器,惟仅在试验中耳。问其曾习何书,则云只《徽言秘旨》、《松弦馆》、《大还阁》、《诚一堂》诸种耳。(见《查阜西琴学文萃》)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五一年,其时管先生的年龄为五十四岁,正是中年。这篇文章对管先生的介绍尽管简短、粗略,却有许多值得分析之处。管先生名平,字吉庵、仲康,号平湖,自称“门外汉”,江苏苏州人。清代名画家管念慈之子。生于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卒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管先生十三岁时遭父丧。十二岁时,管先生的父亲曾教他学过琴,是他学琴的启蒙老师。王迪先生的文章中说管先生“自幼酷爱艺术,弹琴学画皆得家传。”可见管先生的琴和画的启蒙老师都是他父亲。因为管先生的父亲在管先生弱龄之时便去世,管先生从父学得的技艺应该不多,但家学之于一个人艺术历程的影响力却不可忽视。管先生正式习琴的年代不详,按查阜西先生的文章介绍,“及长,从其父之徒叶诗梦受琴。”学了哪些曲子,也不详。而后, “从北京人张相韬受《渔歌》及有词之曲三五”,“为时仅半年”。这说明管先生在向张相韬学琴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否则,要学《渔歌》这样的曲子是困难的。而从张相韬学琴,还学了“有词之曲三五”,说明管先生曾经接触过琴歌。管先生比较重要的老师是近代名琴家杨宗稷,这一段学习的时间较长,“约二年”,学的曲子也多是《渔歌》、《潇湘水云》、《水仙操》等名曲。杨宗稷的老师是近代大琴家黄勉之,管先生向杨宗稷学琴二年,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受杨宗稷的影响。杨宗稷没有录音,但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杨宗稷的儿子杨葆元的琴音中听出管先生与杨宗稷的渊源。对管先生影响更大的应该是天平山的悟澄和尚。管先生遇到悟澄和尚以后,“从其习‘武彝山人’之指法及用谱规则,历时四五月整理指法,作风遂大变。”杨宗稷是成名琴家,又是以教学严格著称的黄勉之的弟子,管先生随杨宗稷习琴,自然接受严格的指法训练和用谱规则。那么,以如此严格的训练基础,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不同的指法和用谱规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悟澄和尚的指法和用谱规则一定有不同一般的妙处。而“作风遂大变”,更明白地说明了这种影响之大。王迪先生这样概括管先生的琴艺渊源:“管先生对古琴艺术研究极深,得九嶷派杨宗稷、武夷派悟澄老人及川派秦鹤鸣等名琴家之真传,他能博取三家水仙操等名曲之长,并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融会贯通,不断创新,自成一家,形成近代中国琴坛上有重要地位的‘管派’。”可见,管先生的琴风由三个重要方面构一是博取各家之长;二是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三是创新。这种概括与查阜西先生文中的内容略有差异,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因为管先生没有留下教琴的教材或操缦的笔记,致使我们今天非常遗憾地不能具体分析他的心得,好在他留下了大量的录音,使得我们可以直接聆听他的琴音,使我们须臾不离他的艺术,这其实是最要紧的。管先生的琴艺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里,我不可能、也没条件详说,只能谈谈自己听管先生琴曲的大概感受,说说我对管先生总体琴风的理解。我说过,古琴的最高境界是“清”,而管先生的琴风,正可以一个“清”字概括。声音是无处逃心的,是一个琴人内心情况的反映,是人格精神的写照。管先生的“清”,首先是人格的清洁。但凡介绍管先生的文章,都不免说到管先生的清寒,但正如桓谭《新论琴道篇》中所说: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对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后贱,昔富而今贫。摈压穷巷,不交四邻,不若身材高妙,怀质抱真,逢谗罹谮,怨结而不得言;不若交欢而结爱,无怨而生离,远赴绝国,无相见期;不若幼无父母,壮无妻儿,出以野泽为邻,入用掘穴为家,困于朝夕,无所假贷。若此人者,但闻飞鸟之号,秋风鸣条,则伤心矣,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未有不凄恻而涕泣者也。”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也再深刻不过。正如“诗穷而后工”一样简单和深刻。管先生的生活遭遇,与雍门周描述的那些不幸之状是一样的,但管先生之高,在于他的音乐有超越悲恻的美,他的音乐有深在的悲苦,但并非形容枯悴之态。清新质朴,是天行健、君子自强的品格。老子说,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延用此说,我以为,管先生的琴乐是大悲若喜。这样的超越,似乎都没有经过任何的纠缠,没有丝毫的自怜自艾,便转化成一种与天地、山水、人格中最美好的品质浑然一体的美,不可名状。恰如刘熙载《艺概》所说:“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他说的是诗人,用以说管先生,也是非常合适的。性情之正、人格之高,是管先生琴艺的根本,有了这样的根本,管先生是自信的,他的琴因而有了清刚之气,乐而不荒,忧而不困。管先生所弹的琴曲中,以“悲曲”居多,《幽兰》、《胡笳十八拍》、《大胡笳》、《离骚》、《乌夜啼》、《广陵散》、《潇湘水云》等,都是失意、愤懑的内涵。但他的演绎却将这种内涵引向于“清壮”,哀痛总是被转化为深沉内敛,缠绵情绪被转化为大的悲悯,成为哀而不伤的境界。“清”,在明清文化,常常只是一种平和雅致的趣味,这种雅趣当然也能远离悲苦,但不免让人触摸不到内在的悲怆,而管先生之清,是沉潜于人格精神之中的清,是比雅趣更高的一种人格境界。管先生有盎然的生活趣味,擅种花草,擅作书画,喜爱民间音乐,甚至玩鸣虫也是一流高手。王世襄先生在《冬虫篇》一文中(见《锦灰堆》)说起过管先生养虫的趣事:古琴国手管平湖,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艺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麻杨罐中喜出大翅油壶鲁,其翅之宽与长,数十年不一见。初售得善价,旋因翅动而不出声被退还。平湖先生闻讯至,探以兔髭,两翅颤动如拱揖状。先生曰:“得之矣!”遂市之而归。不数日,茶馆叫虫,忽有异音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先生曰:“此麻杨的倒拨子’耳,(售出之虫因不佳而退还曰“倒拨子”)众更惊异,竞求回天之术。先生出示大翅,一珠盖药竟点在近翅尖处,此养虫家以为绝对不许可者。先生进__而解答曰:“观虫两翅虽能立起,但中有空隙,各不相涉,安能出音!点药翅尖,取俗谓‘千斤不压梢’之意,压盖膀而低之,使两翅贴着摩擦,自然有声矣。”众皆叹服。先生畜虫,巧法奇招出人意想者尚多,此其一耳。心意之巧,趣味之富,可见一斑。性情如此之人,心中必对生活有喜悦,也必然形之于琴。而琴中所涉社会情感、山水自然,定然有更阔大、更深微的美丽,这些,一定更让管先生着迷,让管先生在于自己情感不离不弃的同时,把深沉的个人情感与广大世界的美融合在一起,在表达的同时实现了超越。这种对一己、对雅趣的超越,非常自然,一点姿态也不去做。能如此,恐怕只能说是天性使然。晋人说,“清正使人自远”。管先生的琴,骨子里清刚清壮,而又有清远之致。清远,是说一个人精神对世俗情感的超越。这种超越,以思辩的方式,或许会落入玄虚寂寞,而以艺术的方式,则在超越自我悲情的同时,与具体可感的美好事物发生联系,以美的形态呈现。管先生的超越,不同于一般的忘怀于山水,不同于简单的依傍。他的琴,更多地有着对历史情感的体贴。当他以琴声去体贴屈原、蔡文姬,去体贴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体贴那些美好而不幸的心灵,体贴山水自然时,他的个人遭际的不幸就与民族的苦难、与众生的盼望融为一体,与不朽的山水相应和,成为一种大的关怀。这种“远”,就不是于情感的逃离,而是美与美的交往。我们在听管先生的琴曲时,总能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清逸之气,一种清越的美。似乎管先生的琴中更多的是山水自然的清新而非人间情感的拘泥。这一方面与管先生的大悲悯、大关怀有关,也与琴曲题材、内涵多山水情抱有关,与管先生重要的打谱多早期琴曲有关,也与管先生的手法有关。管先生打谱的成就,举世公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他所打的谱子多为早期琴曲。《幽兰》取自《古逸丛书》;《长清》、《离骚》、《白雪》、《广陵散》、《获麟》、《大胡笳》据谱为《神奇秘谱》。这些早期琴曲,保留了大量古指法,风格、趣味与明以后有很大的差异。琴曲与中国诗文、绘画、书法等艺术一样,早期的作品质朴、厚重,更重人在天地间的直接感受,植根于生活,取源于心灵,而非生长于既有的艺术传统,因而具有更显著的原创性,艺术手段与表现内容的结合更紧密、更天然,相对于后来的趣味讲求,早期艺术更讲究格调和境界。从艺术历史的角度而言,早期艺术更“古”。琴曲也是如此,早期琴曲声多韵少,右手取音,变化丰富,却又不致于熟腻,左手则简洁,具有清劲、质朴的特点。在前面的章节中我曾说过,打谱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它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创造性,这是琴曲文献多“同名异曲”的原因,也是历代琴曲传承、发展的主要方式。管先生的打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打的许多琴曲,有主要的据本,但将其弹奏录音和据本两相对照,却会发现音、谱字并非一一对应。这种改动,根据多种版本,参证考量而作出,其中也不乏管先生自己的增删。这正是古琴文化的特点,在最高意义上体现了打谱的价值。所以,他的打谱和弹奏,既是精湛的艺术品,也是古琴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管先生右手出音,均是近岳而弹,力度大,劲健清刚,很少出柔和温煦之音,显得非常劲拔、开阔,是往远开张而非往里收缩的。但因为管先生右手指甲不好,几乎没有没有甲音,出音便特别的沉厚,在峭拔的同时,不致于粗厉。古指法用得多,必然变化多,这难免造成细琐,而管先生右手出音既古拗,又在音量上非常统一,始终保持气格上的清正。管先生左手取音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吟猱多用方直而极少用圆柔,而且均是“有板有韵”,有十分严格的规矩。这便化繁为简,使旨在取韵的复杂的吟猱有了统一的个人语言。而且,管先生的吟猱用得并不多,当吟猱便明白清晰地吟猱,不当吟猱则绝不妄动。此外,管先生的绰、注也非常简炼,多取短而少用长。细加留心,可以发现管先生左手的许多取音是直接按本音而不用绰,这与绝大多数琴家取音多用绰有着分明的不同,因而更显得清隽、洁净。古琴取音不易一下子找准本音,所以要借助绰,渐至本音,管先生能直接按准本音,这当然与他无与伦比的功力有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但我认为这更是由管先生对古指法的尊重、由他清劲简明的性格趣味决定的。《神奇秘谱》中有“绰”音,但大多数按音未标“绰”,这显然是古人的一种要求,管先生左手取音,正是按照古谱的风尚而做的。这样,本音和本音之间就少了许多冗赘,少了许多与本质关系不大的所谓“韵味”。对于古琴指法的用意,管先生有独到的见解。我听王迪弹过管先生传授的《渔歌》,其中的拍煞手法很特别,不同于我们听惯的那种爽利的拍煞。王迪先生说,管先生当时的解说是:《渔歌》是归隐之士的精神自况。醉于江湖,心中有所述说,却又觉得不说也罢,于是轻扣船舷,欲说还休。这里的拍煞,应该取此情况。这样的理解,找准了手法与琴曲内涵的内在联系,真是非常微妙得当。在节奏板眼上,管先生也非常有个人特点。他的曲子,节奏规整,韵律方正,急而不乱,缓而不散,语言十分统一。但这种规整,又明显不同于西方音乐的节奏特点,而是以平远、高远、深远的意图,将个人精神均衡地灌注于琴曲展开的每一个阶段。与此相关,管先生弹琴的音色、轻重的变化不大,对比小。听惯了西方音乐的人可能觉得这种音乐比较单调。其实,这正是中国艺术的特点,它不同于情绪化、戏剧化的音乐表达,避免了那种激动的表情,避免了表面的漂亮,使得情感深在,刚正而不粗厉,生动而不过敏,古朴而不枯槁,润泽而不甜腻。管先生的“古”,不是苍古,而是清新之古;管先生的“逸”,不是草逸,而是清逸;管先生的“ 寂”,不是荒寂,是清寂;管先生的“ 健”,不是一般的壮健,而是清健:管先生的“刚”,不是刚硬,而是清刚。管先生的艺术如宋元画,笔笔精到,又略无有句无篇之弊。这有技巧的方面,更反映出人的丝毫不苟且。每一个音、每一个吟猱都有来历有涵义,却又统一于大的境象,遗形得神。管先生对传统琴学的修养极为深厚。他的独特琴风,有着极为扎实的基础。因为对与琴有关的知识、技法掌握得扎实,管先生才有可能在进入中年以后成功地打出那么多古曲,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曲。在今天看来,不懂简谱、五线谱的管先生,在当时录音、辅助记录很差的条件下打成那么多大曲,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须知,这些琴曲,别说“从无到有”艰苦异常地打成功,即便是一个有相当水平的琴家,照着管先生的录音和整理谱把它们全都熟练地学弹成功,也是非常不易的。古人论山水画,有将画家分为逸家、作家者,所谓逸家,即王维、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元四家等天才纵逸的画家。作家即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马远、夏圭、戴进等长于功力者。而兼逸与作之妙者,为范宽、郭熙、李公麟等。前者大致是具有极高天分的艺术家,是开派立宗的人;后者为功力深厚扎实者。只有极少的艺术家能够综两者之长。管先生,可以说就是兼逸与作之妙者。传统“文化”在管先生身上是活的积淀、活的体现,他不是生活在优雅的诗文中,而是生活在生活中,他的琴,植根于中国活的传统中和他自己的生命、性灵中,其清新与自然,有如种子破土而出。管先生的琴,不是舞台表演化的,不是庭园式的,而是万壑松风,是大河宽流,是孤云出岫,是清朴之人立于苍茫天地间的磊落与坦荡。管先生,怎一个“清”字了得!
说不尽的管平湖 作者:郭平《古琴丛谈》